英国:威慑与怀旧
2001年9月11日,纽约(经济观察报书评章)。当飞扬的尘埃在世贸大楼双子塔旁落下,一位不知名的妇女从尘埃中走出来,满身疲倦,向守候在那里的记者问:“为什么?”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和isis国的兴起,让这道难题越发变得沉重。
为什么?十多年来,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马克·里拉的伊斯兰现代化问题,不少政治学者都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不过,这些论述大多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用他者的眼光来看穆斯林国家的。虽不乏卓见,却多少留下一些遗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这些戴着面纱的国家越发显得神秘。作为政治学者,亨廷顿本人其实也不相信当下政治学中,靠数字、模型与枯燥贫瘠的行话搭建起来的“理性选择”,因为文化是感性的,社会是人的。那么,谁来给我们提供感性的认识呢?谁来回答9·11尘埃中那位妇女的悲伤的问题呢?这或许便是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的意义所在。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上千年的君主专制,同时也打断了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革命之后的伊朗,霍梅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成为建国指导思想。从此,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从国家政治到私人生活,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生活,并开展了一场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候,伊斯兰妇女要求必须黑袍加身,掩盖头发,违者处于鞭刑或是拘禁,戴面纱已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行为。1967年巴列维“白色革命”时期的家庭保护法被废除,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子最低结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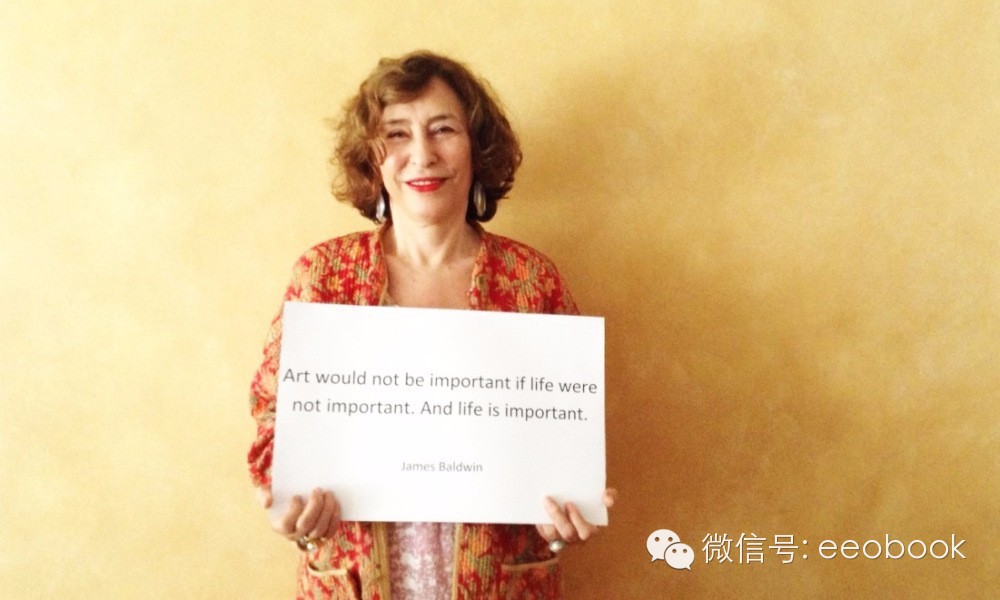
正在这个时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取文学博士学位的阿扎尔·纳菲西回到了祖国伊朗,先后在伊朗的三所大学任教,但因戴面纱的问题而最终被迫辞退。因为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即便在被视为伊朗自由色彩最浓重的学院阿拉梅 塔巴塔拜大学——作者任教的第三所学校,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和活动,都要遭到奚落或是阻扰。在校园门口,有门卫检查女性的服饰和包包,若是发现腮红或是指甲油,轻则遭痛斥重则进监狱接受刑罚,甚至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是吃苹果的姿势性感,而被捕遭受可怕的牢狱之灾。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的阿扎尔·纳菲西,因不堪忍受无所不用其极的骚扰、监视和限制行动,提出了辞职。因为“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当教职员工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纳菲西教授辞职了,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文学课堂,挑选了7位过去的女学生来上西方文学课,秘密地读一些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即便是《一千零一夜》这样的经典的波斯文学,也已经在伊朗被禁止了,她们想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更是不太可能在伊朗书店找到。在挑选这七位女生时,纳菲西教授没有在意她们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七位女生之间既有闺蜜知己也有互相之间水火不容,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勇敢而脆弱交融,爱好西方文学作品。当这七位女生走进课堂,脱去密不透风的黑袍,露出涂着指甲油的手和各自喜欢的衣服,这个秘密课堂便有了纳菲西教授梦想的课堂颜色。在这个课堂上,她们一起读《洛丽塔》,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读詹姆斯,读奥斯丁。此时已经是1995年,离1979年的伊朗革命已经有16年。
因此,与纳菲西教授不一样的是,她的这7位学生几乎从不体验到过自由,甚至一位学生曾被关进监狱7年,但这并不表示她们不知道自由。在纳菲西的秘密文学课堂上,她们在那些西方文学人物身上找寻着自由讨论着自由,谈论“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也因此,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便有了一层德黑兰的色彩: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之邀》的死囚犯辛辛那图成为她们的隐喻。小说中,辛辛那图被迫与狱卒转圈共舞,“极权主义者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强迫人民,包括他们的受害者,成为其罪行的共犯。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无疑是最极端的暴行”。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而不是狱卒强迫他使用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当他捧着自己的头,他周遭虚假的世界,包括行刑台和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崩溃瓦解。在纳菲西教授看来,她们的处境和辛辛那图并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侵犯我们所有的秘密空间,企图规定每个姿势,逼迫我们成为她们的一分子,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处决。”“摆脱圆圈、停止与狱卒共舞唯一的方法是,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也正是在这个秘密课堂上,纳菲西教授和她的七个学生,摆脱了与狱卒共舞。在她们穿着各自风格颜色各异衣服,或是化妆或是不化妆,谈论文学与自己的梦想时候,她们的监狱在她们面前瓦解。

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相比,《我所缄默的事情》讲述的则是自己家族的故事,因此时间也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延伸到上个世纪初,从君主王朝的结束到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从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伊斯兰,这正是伊朗这个古老国家,在世界洪流中,进入现代化的开始。作者的父母来自同一个家族——纳菲西家族,是伊朗以出学者而闻名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保守家庭中唯一的背叛者、伊朗曾经最有前途的两位年轻政治家之一、德黑兰最年轻的市长,其母亲曾是首相的儿媳,亦曾在国会工作的八位女性之一。他们的女儿阿扎尔,自小听父亲讲古老的民族故事和伊朗历史长大,感受伊斯兰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到英国接受教育,此后又到瑞士美国接受教育。因此,伊朗上个世纪动荡的政治环境与变化,给纳菲西家族打上深深的烙印。
实际上,在书末,作者很贴心地附上了“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某个角度上,纳菲西家族历史便是伊朗历史的缩影。在这段家族史中,阿扎尔·纳菲西不仅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与悲剧,而且还将自己最隐秘的事情公布出来,甚至包括小时候遭遇到的性骚扰,和伊朗社会的性压抑问题。没有什么比妇女的变化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变化了:从阿扎尔·纳菲西神秘自杀的外祖母到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读书成为医生的缺爱的母亲、从在美国取得文学博士文凭的阿扎尔·纳菲西到她那些躲藏在密不透风的黑袍下的学生和在两伊战争炮火中长大的女儿,开始迈入现代化的古老伊朗的多舛命运,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几乎都凝聚在伊朗女人的那一块黑面纱上——这其实不是一块布的问题,在阿扎尔·纳菲西看来,这便是自由,一种选择的自由:既可以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祖母那样一生都戴着面纱,也可以不戴面纱在大学课堂上教授西方文学课。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相比,这个面纱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有了一种生命的气息,让人内心柔软。

在这本家族史结尾的部分,阿扎尔·纳菲西告诉母亲,她要写一本书叫《无耻的女人们》献给母亲——大约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一位波斯学者走在路上,沉思,突然被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外国人撞到了,外国人很生气学者的心不在焉,抽了他一马鞭。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要求外国人向学者道歉。外国人上门道歉。为了接待外国人,这位波斯学者不得不借了几件西式的家具,以免让外国人坐在地毯上。外国人一进门,又破坏了波斯人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没有进门脱鞋,穿着靴子就进门了——这让波斯学者终于确认地球是圆的,而道歉似乎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入侵。一连许多天,波斯学者一直在思考他的发现,最后他宣布:“是的,地球是圆的;女人会开始思考,一旦她们开始思考,她们就会变得无耻。”这便是阿扎尔·纳菲西的无耻的女人的意思——“受过教育、不害怕沉湎情欲的女人们,这些女人既包括她们生活中的真实女人,也包括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这个故事几乎可以看成伊朗现代化的一个寓言,女人开始变得“无耻”有着某种现代化的标识意义。作为一位文学教授,阿扎尔·纳菲西在研究伊朗当代作家时还发现,伊朗的现代化与文学作品的现代化是同时开始的,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故事时,因此,文学作品在德黑兰有了一层辛辛那图的色彩。
很显然,阿扎尔·纳菲西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只不过她这本献给母亲的书不叫《无耻的女人们》,而是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情》。在献给母亲的书中,阿扎尔·纳菲西“无耻地”摘下伊朗女人的黑面纱,将曾经缄默那么多年的事情用辛辛那图的语言说了出来,将古老的伊朗在现代化的历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伤痛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便是对911尘埃中那个悲伤问题的一个回答。
纳菲西:若没有阅读的自由,民主就不存在
其实,在抱着一丝希望给她联系的时候,并没有期待能采访到阿扎尔· 纳菲西教授,因为看了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之后,总是有种错觉,她可能不太方便在公开场合出入。谁知,第二天便得到回复,采访地点约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岸的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对面的一家小咖啡厅内,纳菲西教授和她的家人便住在附近,附近便是著名的水门综合大楼,白宫也离这里不远。
穿着一件简单随意的黑灰布长裙的纳菲西教授准时到了小咖啡厅,戴着一对如火的大红耳环,不到一分钟便熟悉了。如她在小说中所说,她的一家都是爱说故事的人,纳菲西确实如此。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她谈了很多,伊朗和她的家,也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及美国给她带来的安全与自由。当然最多的还是她最爱的文学。在她看来,文学与生命一样重要。为此,她和企鹅出版社一起在线上做了一个小活动,鼓励读者与她一起站出来,捍卫文学在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用纳博科夫的话说,“读者生儿自由,而且应该一直自由。”

问:首先谢谢你接受采访。看完你的这两本书之后,很敬佩你的勇敢,同时也担心你的安全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收到过恐吓威胁?在公众场合是否需要主要安全问题?
纳菲西:没有,我在美国啊,我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
问:哦,那就放心了。那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所说的七位女学生呢?
纳菲西:没有。她们很安全。这本书在伊朗没有出版。
问:她们知道你写了她们吗?
纳菲西:我的那几位学生都知道。知道的,我都和她们说了的,她们也知道她们自己是书中的哪一位,只是外人看不出她们是谁。
问:这会给她们带来麻烦吗?
纳菲西: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就有过麻烦。一般只要她们停止活动或是抗议,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如果总是从事什么活动不停下来,那就麻烦了……你懂吗?
问:是的,你似乎在书里也谈到这点,她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自由,甚至无法想象自由,甚至是亲吻,这和过去的中国有点像。
纳菲西:是的。我过去知道很多有关共产主义。1970年代初,我知道,在中国男人女人总是穿一样的制服,毛夹克,他们被告之,个人生活是不允许,这和伊朗确实很像。
问:伊朗革命后,在公众场合妇女必须穿罩袍戴面纱吗?
纳菲西:在19世纪末,伊朗妇女就已经开始为争取自己的权力,在那时,已经有部分地方的妇女摘下了面纱;1935年,甚至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面纱。曼舒做首相的时候,有六名妇女在国会工作。在伊朗革命前夕,伊朗妇女非常活跃,玛南兹· 阿芙哈密成为女性事务部长,保证女性可以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直到1979年伊朗革命。对了,她在1970年代还去过中国。
问:你在《我所缄默的事情》中提到过,你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伊朗宪法革命,你母亲还在国会工作,现在反而……
纳菲西:现在反而倒退了。伊朗实际上是中东第一个立宪的国家。从我祖母那一代人开始,妇女开始为自由斗争,谈论自由。那一代妇女为更加开放的社会而战斗,从那时起,伊朗妇女开始外出工作,开始开会,开始谈论妇女教育问题。到了我母亲那一代,就更自由了;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一下就回去了。所以我很是为我女儿痛心,她没有见过自由……你见过我母亲和我女儿的照片吗?你看,我母亲,她是最早到国会工作的六名女性之一;你看我女儿,戴着面纱……我们倒回去了。
问:是的,我在你这本书里,不仅读了当代伊朗百年史,更是一部伊朗妇女史、文化史。
纳菲西: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将个人史融进文化史中,告诉读者伊朗的生活是怎样的。
问: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第一章叙述了纳博科夫《斩首之邀》,尤其是最后,辛辛那图在行刑台上念着念着神奇的咒语,对抗外面的世界。这是对如今伊朗女性处境的一个比喻吧?
纳菲西:是的,这个我是从纳博科夫那里感受到的。他的祖国,苏联,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和个人自主性的。所以,纳博科夫非常明白谈论具体个人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谈论个人平等和个人独立。我喜欢他,把他用在我的书里,是因为艺术和文学作品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个人,因为它们是在用你独有的语言和你交谈,这是极权社会所害怕的。民主的意思就是允许你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极权政权只想要一种声音,一种方式,声音越多,极权就越弱。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可能出现改变。你想,你又没有枪,又没有坦克,只有政府才有这些东西,你就只能发声,声音让他们害怕。
问:这就是你和你的学生要上这堂秘密文学课的原因吗?只有这样才能停止与狱卒跳舞?
纳菲西:是的。在极权社会,我们总是常常感到压迫,他们变得很强大,我们变得很渺小。然而,在这个课堂,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谈论那些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谈论着洛丽塔和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极权制度在课堂就不存在。我希望我的学生在那里能够自由的思考,而不是总是围绕着宗教,你知道的,她们都是伊斯兰。
问:在《我所缄默的事情》最后一章中,你抄录了自己1997年7月23日那天,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什么是想象的自由?
纳菲西:我总是认为想象和兴趣联系紧密的。因为你要想象,就首先会有好奇,有行动,去寻找人们谈论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是和极权制度相对立的,他们不想让你自由的想象,不想让你去你从没有看过的地方。而想象就会让你和你从未见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当你在阅读美国或是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时,这个美国就不是政府所说的那个美国,而是一个人自己理解的美国。这时,真相是你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什么人告诉你的。因此,想象往往就是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美国不希望奴隶学会阅读,如果奴隶私自阅读,是会受到惩罚的。以前也有很多国家,妇女也是不允许接受教育的。因为一旦你学会阅读,一旦你学会想象,你就想要更多,你就懂得政府学,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这就很危险。
问:你在书中告诉过你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
纳菲西:是的,思考对人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只要妇女一旦开始思考,就会想为什么男人会比自己更重要?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也可以挣钱,我也可以出门,我也很聪明……这样,妇女就会变得很危险,她们就会要求有自己的地位。这不是什么政治体制,很多人也是很多独裁的。许多家庭就是男人对女人进行独裁,如父亲对女儿的独裁。
问:现在的伊朗女孩可以自己选择丈夫吗?
纳菲西:这要取决于家庭。在革命之前,妇女有很多权力,当时合法结婚年龄是18岁。革命后的政府认为父亲有权力决定,女人的结婚合法结婚年龄是9岁。因此,很多农村家庭很早就把女儿嫁掉了。如今的政府剥夺了伊朗妇女的很多权力,要做出改变首先就要改变相关法律。
问:难怪你爱问你的女学生:你是自由恋爱自己选择丈夫……
纳菲西:哈哈哈哈,在伊朗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她们不允许和同龄男人出去,她们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不得不选择。在一些书中我谈论了这个问题,比如奥斯汀的小说。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她的小说非常具有革命性,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因为钱而结婚,而是与自己挑选的男人结婚。18世纪的英国是非常革命的,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说的革命性是个人的,我不是说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人。
问:难怪你们要读奥斯汀。那你为什么给你的学生选择盖茨比和詹姆斯呢?
纳菲西: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盖茨比这部小说讲金钱如何使人腐化,让人自私贪婪。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詹姆斯的两部小说《黛西 米勒》和《华盛顿广场》说的都是一个女人说不。
问:那么洛丽塔呢?
纳菲西:我在书中提到,亨伯特其实并没有看见洛丽塔。如果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们会互相尊重对方,不会想着改变对方,或是把你变成另一个你。但是亨伯特,他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前死去的情人,于是就把洛丽塔变成他以前的情人。这是犯罪,这是一个极权社会的犯罪。这就有些像伊朗政府。他们看不见伊朗妇女,只是把伊朗妇女变成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在极权社会,你就不是你,你成为他们想要的你,这就像是一种死亡。因此,我在谈论洛丽塔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极端卑劣的。亨伯特拿走了剥夺了她的童年剥夺了她的未来。伊朗女孩子也如此,她们的童年和未来也被剥夺。
问:《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四部分有着内在逻辑?
纳菲西:是的,每一部分是谈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在你的国家如何找到自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权力,还包括个人自由和文化自由。我不太相信,如果我们不自我批评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批判世界,同时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只要每一个人变化了,社会才会变化。
问:你还有一本书《共和国想象》马上也有中文版了,你能介绍下这本书吗?
纳菲西:很多美国人读了我的书,总是问我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平等的国家,也许你们需要文学。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还需要文学吗?我想告诉这些人,一个民主国家,若是没有对共和国的想象民主的想象,也是无法存活的。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个人主义不是意味着挣钱,而是意味着个人独立。





